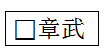
2010年1月3日,接到郭風先生仙逝的電話,仿佛一瞬間,時光倒流,半個多世紀的往事,全都涌上心頭。
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,是1957年。那年,我15歲,正在福清漁溪讀初中三年級。在我所訂閱的文學期刊中,有我終生難忘的《人民文學》3月號,那上面刊登了郭風的《散文五題》。我第一次發(fā)現(xiàn):散文原來可以這樣寫,寫得“像民歌那樣樸素,像抒情詩那樣單純,比酒還強烈”。當語文老師告訴我,作者郭風就是你們莆田人時,我又第一次發(fā)現(xiàn)我的故鄉(xiāng)原來這樣美,美得“像一朵花,開放在藍色的木蘭溪旁邊”。一種對鄉(xiāng)土的摯愛之情,伴隨著葉笛聲聲,像一粒神奇的種子,落在我的心田上,使我為之深深陶醉……
我第一次見到他本人,是1962年。當時,我在福建師范學院中文系就讀。那天,省作家協(xié)會有一場詩文朗誦會,我有幸作為學生代表應邀參加。那天,郭風十分低調(diào)。他彎著腰,縮在臺下的一角,靜聽別人朗誦他的散文詩作品,顯得有點靦腆,有點局促不安,似乎比臺上的人更緊張。我繞到他的側(cè)面,遠遠望過去,發(fā)現(xiàn)他眉宇間似乎有一絲憂郁,但雙眼十分明亮,而且,還有一個正直而又高高隆起的鼻子,這在莆田鄉(xiāng)親中并不多見。當掌聲響起來時,他的臉也突然間紅了起來,似乎很不好意思。后來,主持人要他說話,他大概只講了不很連貫的幾句,內(nèi)容我全忘了,只記得他的口音完全是我最熟悉的最地道的莆田腔,聽起來特別親切。原來,操濃重鄉(xiāng)音的莆田人,也可以寫出那么好的文章,也可以榮登文學的大雅之堂,這一重大發(fā)現(xiàn),對于像我這樣一只正在做“天鵝夢”的“丑小鴨”來說,至關重要,因為他使我的信心為之大增。
我第一次成為他的部下,他的鄰居,是在1978年。當年,我是《福建文學》的新編輯。從此,我在他身邊工作、生活了30多年。30多年來,在我的心目中,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?
我曾經(jīng)在《穆如清風》的萬字長文中,用以下一段話,對他加以概括:
一位溫柔敦厚的長者。一位學貫中西的智者。一位白發(fā)蒼蒼的兒童。一位勤勞儉樸的老農(nóng),一位愛吃地瓜稀飯的老鄉(xiāng)。一位喜歡早起“開窗的人”,一位愛花、愛蝴蝶、也愛榕樹的人。一位充滿幻想的詩人,一位“五官開放”的旅行者,一位使用問號最多的散文家,一位一輩子為孩子們精心制作“點心”的廚師。一位平易近人的老領導,一位循規(guī)蹈距的小公務員。一位從不請人寫序,卻為許多青年人寫序的人。一位不善交際而朋友遍天下的人,一位不愛在公眾場合講話,但卻常常妙語連珠,語驚四座的演說家。一位把生命牢牢釘在“文學十字架”上的人,一位著作等身但卻拒絕炒作的成功者……
以上這段話,每一句都有故事,每個故事發(fā)生時,我都在場,都有幸從中受到教誨,受到啟迪,受到鼓舞,受到鞭策……
如今,他的書還在,故事還歷歷在目,但寫書的人,故事的主人公卻走了。我最可敬仰的老師,最可信賴的朋友,最可親近的老鄉(xiāng),終于走了,走向一個遙遠的不可知的世界。
我望著他的遺照,望著他的遺著,淚眼一片模糊……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