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黃祖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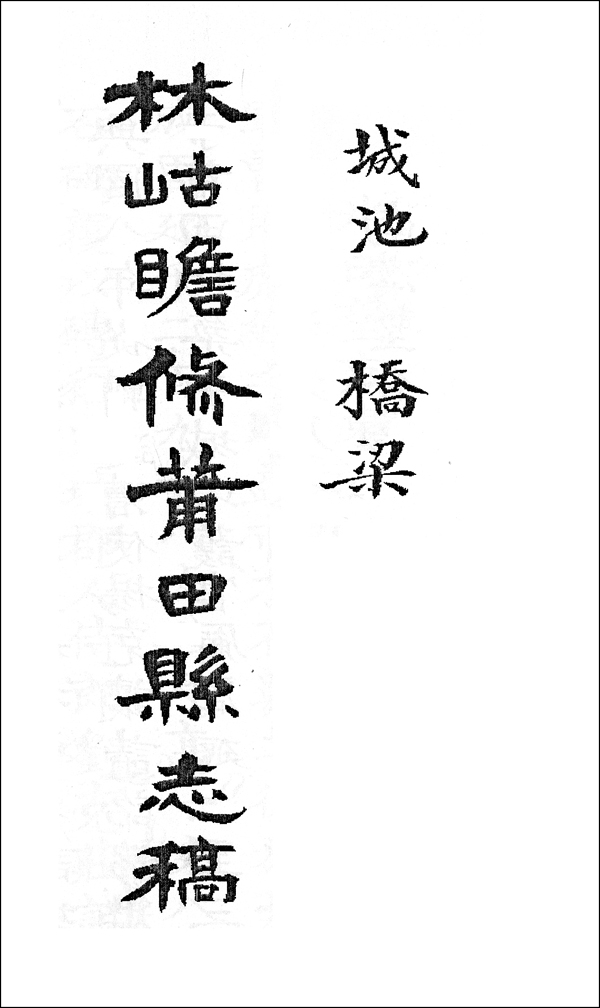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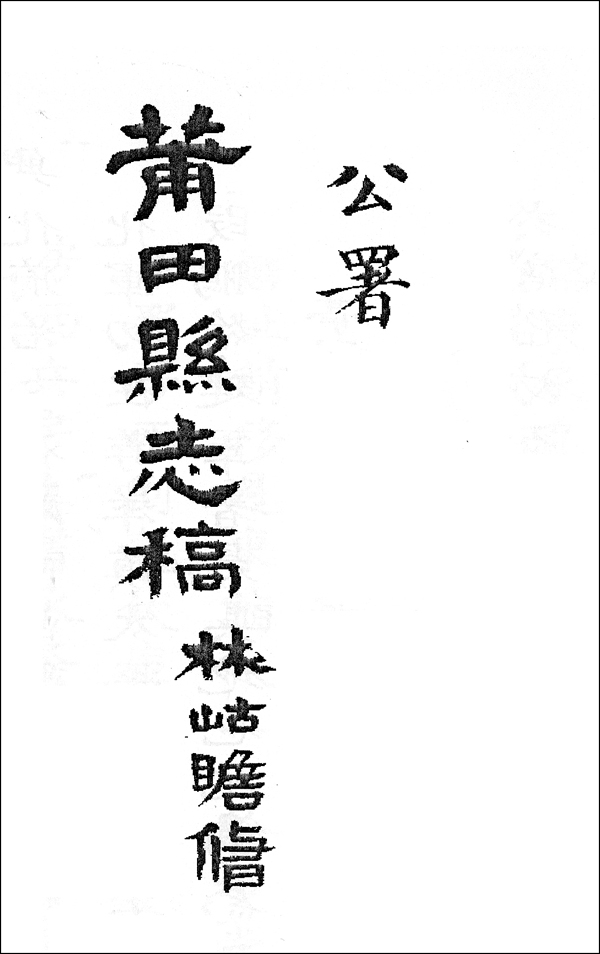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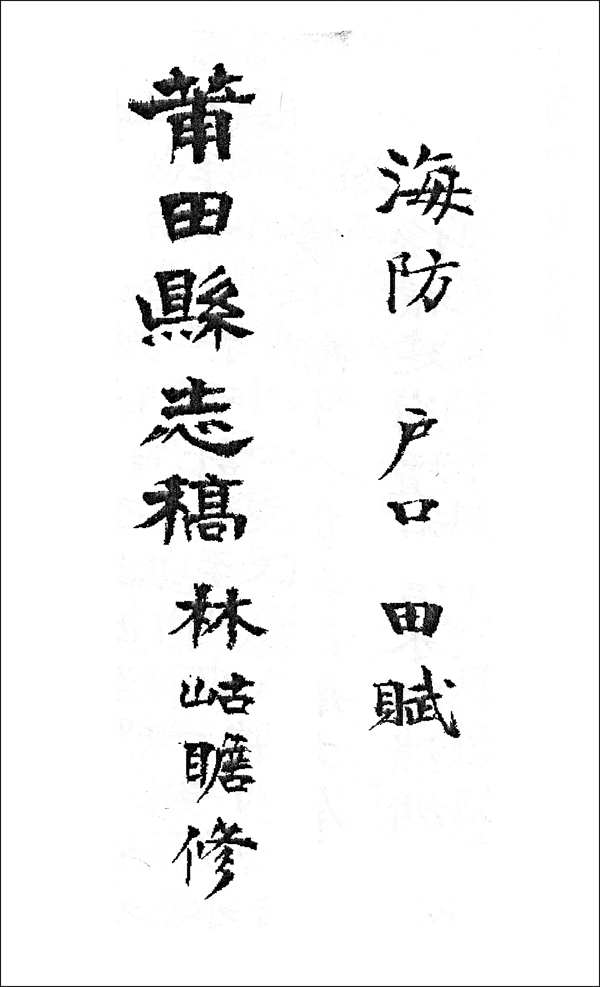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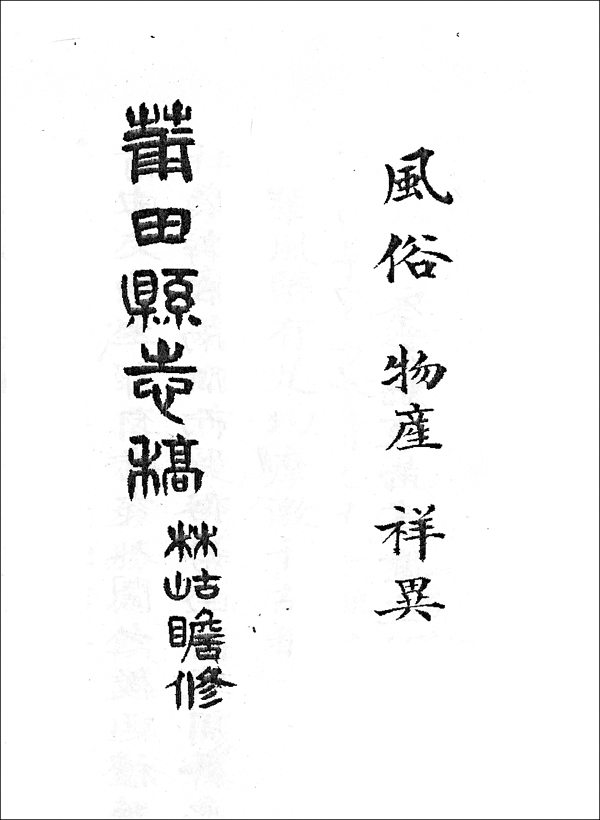

肅順在咸豐七年(1857)擢左都御史、理藩院尚書,兼都統。時寇亂方熾,外患日深,文宗憂勤,要政多下廷議。肅順恃恩眷,其兄鄭親王端華及怡親王載垣相為附和,排擠異己,廷臣咸側目。咸豐八年(1858)戊午,調禮部尚書,仍管理藩院事,又調戶部。會英法聯軍犯天津,起前大學士耆英隨欽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納往議約。耆英不候旨回京,下獄議罪,擬絞監候,肅順獨具疏請立予正法,上雖斥其言過當,即賜耆英自盡。大學士柏葰典順天鄉試,以縱容家人靳樣舞弊,命肅順會同刑部鞫訊,讞大辟,上念柏葰舊臣,獄情可原,欲寬之;肅順力爭,遂命斬。戶部因軍興財匱,行鈔,置寶鈔處,行大錢,置官錢總局,分領其事。又設官號,招商佐出納,號“乾”字者四,“宇”字者五。鈔幣大錢無信用,以法令強行之,官民交累,徒滋弊竇。肅順察寶鈔處所列“宇”字五號欠款與官錢總局存檔不符,奏請究治,得朦混狀,褫司員臺斐音等職,與商人并論罪,籍沒者數十家。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,褫關防員外郎景雯等職,籍沒官吏亦數十家。大學士祁寯藻、翁心存皆因與意見不合,齮龁不安于位而去,心存且幾被重罪。
肅順日益驕橫,睥睨一切,而喜延攬名流,朝士如郭嵩燾、尹耕云及舉人王闿運、高心夔輩,皆出入其門,采取言論,密以上陳。于剿匪主用湘軍,曾國藩、胡林翼每有陳奏,多得報可,長江上游以次收復。左宗棠為官文所劾,賴其調護免罪,且破格擢用。文宗之信任久而益專。
自咸豐八年(1858)戊午,桂良等在天津與各國議和,廷議于“遣使入京”一條堅不欲行,迄未換約。咸豐九年(1859)己未,乃有大沽之戰,敵卻退。咸豐十年(1860)庚申,英法聯軍又來犯,僧格林沁拒戰屢失利,復遣桂良等議和。敵軍近逼通州,乃改命怡親王載垣、尚書穆蔭往議,誘擒英官巴夏禮置之獄,而我軍屢敗之余不能戰,車駕倉猝幸熱河,廷臣爭之不可。事多出肅順所贊畫,遂扈從。洎敵軍入京師,恭親王留京主議和,議既定,敵軍漸退。留京王大臣吁請回鑾,肅順謂敵情叵測,力阻而罷。肅順先已授御前大臣、內務府大臣,至是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,署領侍衛內大臣、行在事一以委之。
咸豐十一年(1861)辛酉七月,上疾大漸,召肅順及御前大臣載垣、端華、景壽,軍機大臣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入見,受顧命,上已不能御硃筆,諸臣承寫焉。穆宗載淳即位,肅順等以贊襄政務多專擅,御史董元醇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。肅順等梗其議,擬旨駁斥,非兩宮意,抑不下,載垣、端華等負氣不視事。相持逾日,卒如所擬。又屢阻回鑾。恭親王至行在,乃密定計。九月,車駕還京,至即宣示肅順、載垣、端華等不法狀,下王大臣議罪。肅順方護文宗梓宮在途,命睿親王仁壽、醇郡王奕譞往逮,遇諸密云,夜就行館捕之,咆哮不服,械系。下宗人府獄,見載坦、端華已先在,叱曰:“早從吾言,何至今日?”載坦咎肅順曰:“吾罪皆聽汝言成之也!”讞上,罪皆凌遲。詔謂:“擅政阻皇太后垂簾,三人同罪,而肅順擅坐御位,進內廷出入自由,擅用行宮御用器物,傳收應用物件。抗違不遵,并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,詞氣抑揚,意在構釁,其悖逆狂謬,較載坦、端華罪尤重。”賜載坦、端華自盡,斬肅順于市。
林揚祖歷任京官十八年,外任十一年,所任皆要職,嘗得旨有“辦事認真,操守端方”的嘉獎。
穆宗同治元年(1862),奉旨以原品致仕。其時直道安貧,清介絕俗,奈何關山萬里,盤纏不足,至于舉債,乃不足,揚祖乃以高利貸向山西匯局貸款,始克成行。同治三年(1864)甲子旋里,抵家后典賣衣物還債。揚祖居家,熱心桑梓教育,在興安書院、擢英書院及仙游、廈門、永春等地掌教,為書院山長,對童生課卷,皆親手批點,榜發,召童生來,面喻其優劣,教以讀書為文之法,歷二十三年而不倦。
揚祖事母至孝,生母年青孀居,柏舟矢志,撫育幼子成人,翁氏得享遐齡,彌留之際,嘗召揚祖與全家子孫至病榻前云:“我們家中人丁旺盛,已不像從前孤單,但有一事應該牢牢記住,即如果家中有一男不幸夭逝,其年青媳婦,必須立即準其改嫁,切勿以門風或面子關系,令其守寡孀居……”翁氏的遺囑,確是老人家留下的開明警語,也是自己在舊禮教桎梏下孤苦守寡的泣血傾訴,聞之令人潸然下淚。揚祖家居在教書侍親之余,著有《歸食日記》,文如其人,人如其文。主持編修同治《莆田縣志稿》。其志稿共分二十一卷:卷一城池,橋梁;卷二公署;卷三海防、戶口、田賦;卷四風俗、物產、祥異;卷五職官;卷六官績;卷七政績;卷八學校、書院;卷九兵制、武功、屯田;卷十科舉;卷十一諸科;卷十二薦辟;卷十三封蔭、應例、年勞;卷十四名臣;卷十五列女;卷十六列女(增);卷十七古跡;卷十八隱逸、塚墓、寺觀;卷十九祠廟;卷二十典籍;卷二十一叢談。
莆陽才女陳淑英,系林揚祖的表嫂,著有《竹素園集》。其撰《課子》詩曰:“浮生日月付游移,皓首窮往悔已遲。千古英雄書得力,勛名大半少年基。”其二詩曰:“立業先宜立志堅,筆為鋤耒紙為田。世間除卻文章富,縱有千金不值錢。”其撰《戒子》詩曰:“持家勤儉是先籌,境遇豐屯不自由。花酒每將豪杰喪,詩書全在苦中求。安時須切思危計,長處應留補短謀。兒輩果能循簡樸,庶堪世業紹箕裘。”
揚祖為撰《竹素園集》序:“淑英女史陳表嫂、余母黨中表翁樸園茂才之配也。樸園諱煥文,邑增廣生。博通經史,善屬文,兼諳詞賦。余發汴省時,樸園在署代辦家務,常為余言嫂陳氏亦能詩,自號淑英女史,有《竹素園集》,惜未帶入行篋相就正。余素念陳嫂持家有法,佐夫讀書知禮義,能文章。教二子皆成大器,久為鄉人所推重。余母翁太夫人愛之,敬之,稱道不衰。不知其能吟詠也。歲甲子,余罷發旋里,樸園公已沒,陳嫂命其子兆蘭、兆熊,屢以時文質證于余,時兆蘭已食餼,兆熊亦補邑弟子員矣!兆蘭兄弟因袖其母《竹素園》示余,余熟讀幾回,詞皆澤古品不入庸,特以吾邑俯處海隅,即文人學士以古近體詩所擅此者,亦罕有積成卷秩,付之梨棗,不意閨閣中能以和聲鳴畫,而措詞溫厚,不但藻麗為工,洵風教所開也。且其人即為余中表至親,豈特蘭水壺山為之生色乎!余見集中遠近士大夫題跋,珠璣滿卷,金石成聲,則《竹素園集》一集,固不待余之稱揚,然見詩而綴一辭,余固不可無言也。因詩而敬其人,余又不能已于言也,由是益信吾母知人不輕推許,有所譽必有所試矣。今兆蘭昆仲欲闡揚母教不憚,廣求題序,是亦顯親一大義也。余讀其母之詩,烏得不附名于簡未哉!爰不揣固陋而為之序。同治六年(1867)丁卯立冬日覺口。林揚祖拜撰。”及陳淑英卒,名士劉尚文挽陳淑英聯云:“一朝絕筆椒花頌,千載道篇《竹素園》。”
林揚祖雖年老讀書尤勤,每日閱讀史鑒二十余頁,手不釋卷,通宵秉燭觀書,亦無倦意。有時手中茶杯竟經常落地,鏗然有聲,習慣成自然,家人常引為談笑。日習柳公權秘塔百余字,作《歸食日記》數則,雖盛夏嚴寒不廢。自云:“終年賴掌教束脩(喻教師報酬之代稱)二百千以自給。”聽者或不信,揚祖也不求其信。其為清代著名書法家、史學家。至于勤奮刻苦的精神常令后生汗顏。揚祖有時外出訪親探友,扶杖步行,從不坐轎,衣飾樸素,見者不知其為二品大員。其時左宗棠隨軍入閩經莆田時,揚祖亦未參加迎送,其傲岸處令人稱奇。且為人十分謙和,每遇里中或親戚的喜喪之事,必親自前往慶吊,見貧無以為生者,輒施以澤惠。
西巖寺坐落在雷山西麓,前身乃明禮部尚書、國師陳經邦別墅。明亡清立,其孫鐘岱剃度為僧,與師超嵩改別墅為寺,名為“西巖廣福寺”。昔時巖景別致,素以夕眺著稱,號稱“西巖晚眺”,譽為莆田二十四景之一。道光十三年(1833)癸巳,西巖廣福寺重建大雄寶殿。時過境遷,僅隔四十一年,即穆宗同治十三年(1874)甲戌,林揚祖、林壽熙捐金助僧懷靜重修。揚祖為大雄寶殿題撰楹聯。上聯右額首同治甲戌季春吉日“廣福田須憑心地,安黎庶以格蒼穹”。下聯左側落款“里人林揚祖沐手敬題”。
重修平海舊衛學圣廟落成,其撰《重修平海舊衛學圣廟碑記》:伊古祀事,有其廢之莫敢舉,有其舉之莫敢廢也。平海在城東九十里,有明寘衛設學,我朝順治年間(1644-1661)因之。諸生弦誦其中,掇巍科者不絕。康熙罷衛,以學額猶存,別營城西射圃地寘學,即今改為興安書院者,人往往稱“平學”,沿其舊也。嗣以學校統諸郡邑,衛學額也裁。蓋學與衛并廢者,百余年于茲矣。雖然,衛學裁而平海學宮固未盡毀也。已廢之衛與學莫敢舉,而平海舊學崇奉先圣、先師,安妥神靈之所,又莫敢廢也。但己地不立學,不立宮,不致祭,春秋屢易,屋宇傾頹,上雨傍風,無所蓋障,而圣廟之立亦失。乾隆年間(1736-1795)、居人夜見宿莽有光發,視之得故宮先師主。聞之官,太守范公宏遇率紳士進入興安學,旋又奉主歸故廟,則太守灝公聽近海諸生吁請重建。
道光二十年(1840),平海縣丞邊君錫齡捐廉倡修,勸暮金得五百有奇,葺大成殿,傍及文昌宮,工未竟而財告匱,蓋舉之而猶有待也。癸卯(1843)歲月,海外漂大木至,一桅一舵,無所歸,應歸公,久寄海岸。時圣裔山東昭慈權莆邑,或以木竟之工清,公清貧無能助,籌以桅、舵價藏,乃事未成孔公去,蓋欲舉而有志未逮也。甲辰(1844)冬,郡司馬劉公辦事至平海,諸生率相告,公欣然臨海濱,起桅、舵付售。諏吉鳩工……學故也,祀則舉矣。夫以既裁之學,未毀之宮,亡而復存之主,皆二太守或為之迎入新學,或為之奉歸故廟,是舉其所未盡廢,舉之者未為失禮。茍舉矣,而終于廢,大違于禮矣。嗚乎,莆俗信鬼神,輒醵金事神,刻桷丹楹以妥之,俎豆鼓鐘以享之,況圣如孔子,生民未有其教為萬世所推尊,其廟為國朝所崇祀。學雖廢而宮猶在,出主于莽,得木于洋,海若效靈,顯應迭見。天之心也,人之愿也。倘借口曰:“廢學舊廟,無庸再修。”豈有識者所忍言哉!是役也,劉司馬告余曰:“奉谷、武盛二里,地近海隅,人多稚魯,每采風所至,接見詩書之士,相與論道德,談文章,輒油油不忍去,有古儒者風。濱海諸生,離城既遠,戀戀于舊學故廟,思欲表章圣道,扶植斯文,可以振聾聵,可以息澆淳、其盛舉也,子不可以不書。”余曰:“唯唯。”此余所樂道也,謹退而載筆焉。劉公,江蘇武進人,官興化糧捕通判兼管水利,有政聲。姓、字、爵應與邊丞、孔令并附勒石,以垂永遠。是為記。
賜進士出身、巡視北城御史、莆田林揚祖撰記并書。
莆陽舊俗若逢過年或正月十五元宵,城內各地紅燈高照,張貼燈謎互猜,已成文人雅士競相角斗智慧之時尚,興趣甚濃,此老(揚祖)亦未能免俗。揚祖喜歡親手撰燈謎,任人猜射,其一題為:“人字下面一點。”射四書句,謎底是“既不能令,又不受命”。有士子宋琢堂猜射為:“嬖人有藏倉者阻君,君是以不果來也。”所射新鮮活潑,較原謎底尤佳,揚祖遂以珍藏之端硯一方贈送。
德宗光緒九年(1883)正月二十二日,揚祖卒于府第,享年八十五。揚祖生有五子,后代以揚祖的格言“壽以仁為本,忠堂孝立功”排輩。長子壽熙,優貢生,官陜西潼關撫民同知,左宗棠用兵新疆,襄辦軍需,于勤務著卒于任。次子壽勛,附貢生,試用訓導。三子壽煦,咸豐五年(1856)舉人,入內閣中書。四子壽燕,邑庠生。五子壽照,戶部候補主事,監督京倉,庚子拳亂卒于京。
林府新第坐落于廟前街東側,坐南朝北,為雙座七間廂加護厝和后供堂。前院用規格青條石鋪成長方形大埕,為莆陽古民居建筑,獨樹一幟,風格注重士大夫宅第之古樸大氣,高昂壯觀。石埕三面圍墻,北面為院前方的照墻,東西兩墻則各開一個石框儀門,西門臨廟前街道,東門可通羅巷里直達后街。宅第的建筑布局和梁架結構,充分凸現莆仙民居的傳統風格。它的主屋建在高約0.7米的石砌臺基上,故比普通單層建筑顯得高昂。第一進前廊寬敞,廊柱粗壯,大門高大。廊檐梁架及斗拱、雀替等雕飾簡潔大方。大門額的懸匾已摘毀,僅余門簪一對。正房和廂廳、重廂廳的前窗均采用古典式的拼木花格窗欞。外墻自下而上砌四層條石、五層紅磚,頂層以黏土夯筑,外加白灰抹面,全墻形成青、紅、白相互搭配的基本色調。正厝屋頂作三段脊、高低檐,但只有其中段作雙頭翹脊。這種法式在莆田實屬獨創,如不登高俯瞰,還真看不出。上廳依例敞口,兩廂有廊道通向廂廳和護厝。東護厝的前段之間原是林揚祖的讀書屋,其內外裝修亦相當樸素。這與林揚祖少年失怙、出身貧寒有關。
在林揚祖宅第的東邊后退一點,還有一座坐向相同的二進五間廂大厝,據說是林揚祖族弟之宅。此宅大門卻建在宅右前角,即東儀門之外,故進大門還要穿過儀門才能到達前院的大埕。該故居雖歷經百年風雨,卻依然完好,可以說是一座標準的莆田士大夫宅第。其廊檐雕飾、卷書彩繪、窗欞花格均完好無損,只是色彩褪了許多。此宅已作為林揚祖故居的附屬建筑,一起于1993年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揚祖其生平事跡可見《晉安林莆田長城金紫族譜》《廣西古代職官資料匯編》《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》《陜西省志》《福建興化文獻》《莆田市志》《秀嶼區志》,以及乾隆《莆田縣志》、同治《福建通志》、民國《福建通志》、民國《莆田縣志》。 (完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