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鄭國賢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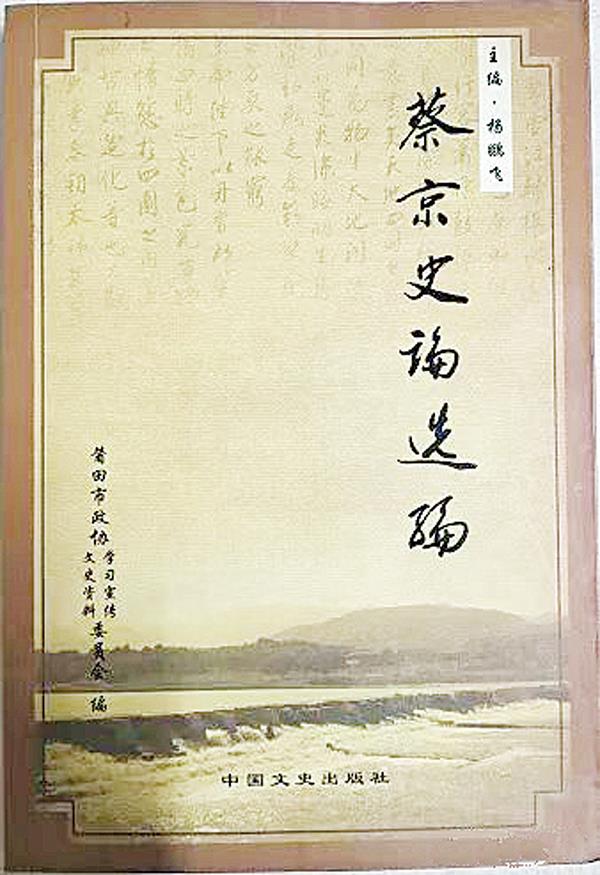
我其實并未看過楓亭“游燈”。印象較深的倒是宋詩宋詞中“上元燈節(jié)”的描繪;少時看《水滸》連環(huán)圖,看到浪子燕青在上元之夜?jié)撊霒|京李師師的家中,關(guān)心的是燕青通過李師師打通宋徽宗的關(guān)節(jié)如何招安,關(guān)心的是梁山英雄好漢們的命運,連李師師家中如何燈紅酒綠都不在意,更不會關(guān)心街上熱鬧的花燈了。有一年在遠離楓亭幾十里的莆仙交界處一個小村看到游燈,入夜時分,村民們扛著燈架游弋于木蘭溪兩岸,沒有鑼鼓,也不放鞭炮,寧靜的夜色中昏黃的燈龍在緩緩移動,有一種遙遠的古老的氣息微微傳來……
猛然記起多年前已有一篇《難忘家鄉(xiāng)龍燈游》,出自我一位朋友的筆下:
“每年元宵節(jié),我的家鄉(xiāng)利角村及毗鄰的海頭、東海、大埔、東沙四個村,都要舉行一場熱鬧非凡的游燈盛會。每個村至少要出一條燈龍,燈龍由燈頭、燈身和燈尾組成。燈頭由各種造型別致的大燈籠點綴而成。燈身由一節(jié)一節(jié)的燈架集合而成,每節(jié)燈架上有八至十盞不等的點著蠟燭的燈籠。一節(jié)燈架由一戶人家舉著。燈尾呢,有的是抬菩薩,有的是敲鑼打鼓。每當元宵節(jié)夜幕降臨時,一條條的燈龍穿梭于各個村莊之間,那披紅戴綠的男男女女,那飛光流彩的燈海,那熱熱鬧鬧的鞭炮聲,那五彩繽紛的煙花,令人如醉如狂。”
朋友姓蔡,卻與他的幾萬蔡姓鄉(xiāng)親一樣,大都忌諱為蔡京的后裔,而拜宋代清官蔡襄為祖。為此,蔡氏族人曾與莆仙文史界的老人們多次鬧得不可開交。
文人當面不敢堅持,過后都會不無譏諷地提起秦檜的后人秦澗泉,以及他在西湖岳飛墓前的那對名聯(lián):“人從宋后羞名檜,我到墳前愧姓秦。”
莆仙人忌諱蔡京,以至于有關(guān)蔡氏一門在長期當權(quán)時引進東京戲曲藝術(shù)回故鄉(xiāng)的資料,散失在史海的茫茫煙波之中;只有楓亭楊亞其老人保存一本一直秘不示人的《連江里志·上卷》抄本(楓亭舊名連江里)。我們這次找到楓亭舊街見到他,老人經(jīng)過一番猶豫,終于從樓上拿出這個抄本,該書第二條就是:“《山房遺稿》卷五載:宣和末,蔡攸(蔡京長子)以燈事色樂游楓亭,置畫舫于江上,使教坊女弟妝扮故事以侑酒。”(江是楓江,流入湄洲灣,不是木蘭溪。)
這則簡單的文字傳達了兩條重要歷史信息:一是楓亭及其鄰近地區(qū)獨特的元宵游燈習俗源于宋代;二是蔡京父子(特別是蔡攸)是戲劇由北方引入莆仙地區(qū)(包括閩南)的關(guān)鍵——“使教坊女弟妝扮故事”。
莆仙戲的源頭充滿著太多的傳說,而真實的來歷卻資料奇缺,這不能不歸因于蔡京。
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,對神圣或神奇的東西一貫持懷疑態(tài)度。一個偶然的機會,我看到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小冊子,內(nèi)載宋方天若《木蘭水利記》,編者明代鄭思亨跋其云:“……莆人遂諱京功,并諱天若記。予不以人廢言,姑特存之。”
“莆人遂諱京功”之說吊起了我對蔡京的好奇。我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翻閱了《宋史》《莆田縣志》《仙游縣志》和《仙溪志》,得出結(jié)論:所有這些傳說都緣于“諱功”,這種脆弱幼稚的地域文化心理,類似于當代的“血統(tǒng)論”。而歷史的真實是:蔡京執(zhí)政二十三年,任命了不少親信(含莆仙籍官員)擔任福建地方官,這些地方官秉承他的旨意,建造了大量的水利橋梁等公共設施,因而,在北方連年戰(zhàn)亂的大背景下,福建“民安土樂業(yè),川源浸灌,田疇膏沃,無兇年之憂”(《宋史·地理志》),海上交通和貿(mào)易獲得了極大的發(fā)展。南路入粵東,北路抵永嘉,西北至贛、浙,泉州港成為“東方第一大港”。
限于篇幅和能力,我無法梳理北宋新舊兩黨交爭的是是非非,也無能力為蔡京的是非功過一一作出評判,只提一下蔡京當權(quán)時“狠抓落實”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。“貧有養(yǎng)、病有醫(yī)、死有葬。”居養(yǎng)院以處鰥寡孤獨,安濟坊以醫(yī)民之貧病者,漏澤園以葬貧亡者與客死荒野者。
這樣的好政策未必得到認真的貫徹,還可能受到頑強的抵抗,如果受到“名人”的反對,那后果就更糟了。著名詩人陸游在《老學庵筆記》中說:“崇寧……置居養(yǎng)院、安濟坊、漏澤園,所費尤大,朝廷課以為殿最,往往竭州郡之力,僅能枝梧。”老百姓還要編歌謠罵娘:“不養(yǎng)健兒,卻養(yǎng)乞兒;不管活人,只管死尸。”
長期的官場斗爭鍛就了蔡京的鐵腕性格,“蓋軍糧乏、民力窮,皆不問。若安濟等有不及,則被罪也。”因而州縣領(lǐng)導“寧左勿右”,紛紛“奉行過當”。最后倒霉的不是別人,而是蔡京。國家滅亡了,沒有人敢去罵那位“風流天子”,而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在蔡京頭上。當時的風氣是:“今日江湖從學者,人人諱道是門生。”
蔡京一生喜愛莆仙音樂和戲劇。激烈的政爭之余,童年熟悉的旋律,是撫慰心靈消解鄉(xiāng)愁的靈丹妙藥。《拾墨記》說:“蔡京每有宴會樂工輒奏鄉(xiāng)音。”《連江里志·事類》也說:“蔡太師作壽日,優(yōu)人獻技,有客以絲系童子四肢,為肉頭傀儡戲。”
世上無人不好高。權(quán)力可以使人得意忘形,更何況是權(quán)傾朝野,一人當軸之時,《東京夢華錄》卷六載:“左樓相對,鄆王以次彩棚幕次;右樓相對,蔡太師以次執(zhí)政里幕次……諸幕次中,家妓競奏新聲,與山棚露臺上下,樂聲鼎沸。”
不受制約的權(quán)力的危險性,嫁接在第二代身上,往往更加可怕。蔡攸把乃父的特權(quán)發(fā)揮得淋漓盡致。攸“得預宮中秘戲,或侍曲宴,則短衫窄褲,涂抹青紅,雜倡優(yōu)侏儒,多道市井淫蝶謔浪語,以蠱帝心。”(《宋史》卷四七二)“宣和間,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,自為優(yōu)戲。上作參軍趨出,攸戲上曰:‘陛下好個神宗皇帝!’上以杖鞭之曰:‘你也好個司馬丞相。’”(周密《齊東野語》)
甚至還有出格得離譜的言行。《宋史》記載:徽宗封了個副宣撫使讓蔡攸跟童貫去討伐燕山,年輕的蔡攸高興得不得了,認為此行獲勝唾手可得。臨行前到宮里向徽宗告辭,見徽宗身邊的嬪妃實在漂亮,竟不提打仗的事,而指著那兩個嬪妃說:“我打贏了這場戰(zhàn)爭回來,您把她們賞給我。”徽宗聽了并沒有不高興,反而笑了。
物極必反,盛極必衰。金兵攻陷汴京,徽宗退位南逃,欽宗執(zhí)政,亡國的罪責誰來負?皇帝是不能有錯的。于是,蔡京作為“六人幫”之首被流放,行至潭州(長沙)而死。死前曾作《西江月》,詞云:八十一年住世,四千里外無家。如今流落向天涯,夢到瑤池闕下。玉殿五回命相,彤庭幾度宣麻。只因貪戀此榮華,便有如今事也。
鳥之將死,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,其言也善。短短八句,足可謂之一部中國版的《懺悔錄》。
蔡京死后,執(zhí)政者說蔡攸之罪不減乃父。乃下詔貶至萬安軍(廣東萬寧),后派人把他殺了。還連累他的弟弟,欽宗在殺他的詔書下加了三個字“亦然”。
事隔四十一年南宋高宗下詔,把拘管了多年的蔡京家人“放令逐便”。有意思的是,同時解放的還有忠臣岳飛的老婆孩子。重獲自由的蔡京家人遵照他的遺愿,將其遺骸運回家鄉(xiāng)楓亭,安葬在赤湖(今九社村地界)。
幾年前的正月十五,在午間朋友聚餐時,我們就《三希堂法帖》中的蔡京的書法談起他的為人種種。飯后,直奔楓亭。一路打聽,終于來到楓亭鎮(zhèn)九社村的一片枇杷林中。蔡京墳前的石馬石羊已被他的鄉(xiāng)親偷光賣光,唯有仙游縣政府立的石碑沒人要,卻也被推倒在地。當?shù)鼐派绱迨?/span>“山地開發(fā)先進村”,墳地的龍眼樹下,又加栽了密密麻麻的枇杷樹。
離開蔡京墳,我們從蔡氏故里赤嶺東宅村穿過,跨過一道小橋,越過九澗,來到了梅嶺腳下。在村里一位老者的引導下,找到了蔡氏祖墳。老墳的墳頭比普通的墳頭大了一倍多,被高及人頭的荊棘和雜草包圍著,是多少年無人疏理的結(jié)果。只有墳頭之上,有人新近壓上一疊紙錢,在山間的微風中輕輕顫動。老者告訴我們:“蔡家祖墳大風水是座筆架山,左右山脈有五瓣,猶如五條蒼龍直插赤湖深淵,有‘五龍盤珠’之美名,所以蔡家出了左右兩丞相。”——這就是無人疏理祖墳,卻有人為其壓紙錢的解釋。
最近我再次來到楓亭,在蔡京墓地,枇杷樹已不見,龍眼樹下曾被推倒的石碑已重新豎立。石碑前,是一叢叢剛剛燒燼的香灰,那裊裊輕煙仿佛還未散盡…… (備注:本文于2011年被收錄到《蔡京史論選編》。有刪節(jié)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