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白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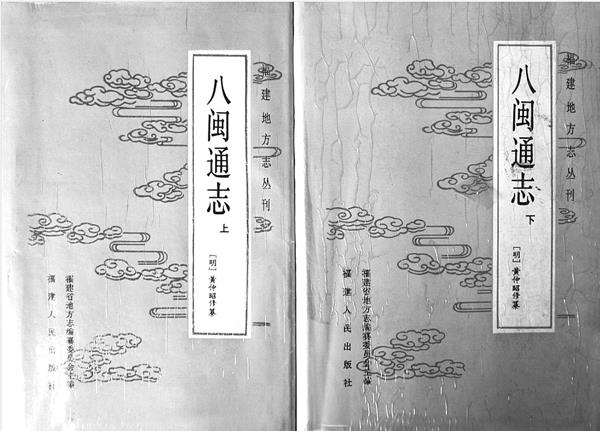
誰是莆田歷史上的第一個進士?這是以往有過不少誤解和爭議的問題。明代邑人周華在《游洋志·人物》中記載:“金鯉,字伯龍,清源東里白鶴人,登武德二年(619)庚辰進士第(按:武德三年才是庚辰年,記載明顯有誤)。”古清源東里白鶴,屬于唐代泉州莆田縣境內,就是今天的莆田市涵江區新縣鎮白鶴村。為此,在莆田市的第一輪修志中,不少編寫者都沿用“金鯉是莆田歷史上第一個進士”的說法。如新編《莆田縣志》載“金鯉,唐武德三年(620)進士”;新編《仙游縣志》載“金鯉,唐武德二年(619)進士”;新編《莆田市志》與新編《莆田縣志》的記載也是一樣的。還有《興化進士》《莆田史話》《莆田市名人志》等邑人出版的書籍,均持同樣的觀點,以至于后來的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訛傳訛。
顯而易見,《游洋志》的記載是有問題的。首先,從該志的成書背景看。宋太平興國四年(979)設置興化縣,縣治在游洋(今仙游縣游洋鎮)。元皇慶二年(1313),興化縣治由游洋遷到廣業里湘溪(今涵江區新縣鎮)。明正統十三年(1448),撤銷了興化縣。該書的作者是明代莊邊赤石村(今屬涵江區莊邊鎮)的周華,字子實,號滄溪。他在興化縣裁撤之后,編著《游洋志》(八卷),并未刊印,僅有殘缺之抄本。民國25年(1936)邑人張國樞根據馬堃家藏的抄本,補缺鉛印刊行,改名《福建興化縣志》,增印鄭貞文、張琴之序,其目的是“提議恢復興化縣治。”正如邑人末科進士張琴在序言中所說:“游洋人張君國樞……聯請恢復縣治,省政府未報可,仍重刊是編,改稱《興化縣志》。”由于出版的動機是為了恢復興化縣治,故在手抄本的基礎上增加一些唐代的內容是有可能的。
對此,曾經有莆田學者提出質疑,甚至連該書的點校者邑人蔡金耀也認為書中的唐代人物資料靠不住。因為在《游洋志》卷四“人物·薛巒”條又云:“薛巒,字山甫,清源東里鳳搏人。其先祖唐右輔闕(薛)令之,居長溪縣,神龍二年(706),始以閩人登進士第。……太平興國五年(980)舉進士,邑人登第自公(薛巒)始。”這段史料記載清楚地告訴了我們,薛巒的先祖薛令之于唐神龍二年登第,是福建的第一位進士;薛巒于宋太平興國五年登第,是興化縣的第一位進士。同一本志書出現兩種不同的結論,自相矛盾,耐人尋味。
其次,從福建地方志的記載看,宋代黃巖孫的《仙溪志》卷二“進士題名”也載:“唐重進士科,莆始于林藻、歐陽詹,仙游始于陳乘、楊在堯、陳光義。”這是林藻為莆田第一位進士的最早記載,而此書沒有金鯉登第的任何信息。明代邑人黃仲昭的《八閩通志》卷七十二“人物”亦云:“林藻,字緯乾,貞元七年(791)登進士第,郡人登第自(林)藻始。”也就是說,莆田的第一位進士是林藻,該書也沒有金鯉登第的有關記錄。
《八閩通志》是現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志,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價說:“福建自宋梁克家《三山志》以后,記輿地者不下數十家,唯明黃仲昭《八閩通志》頗稱善本。”該《志》“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,在地方志中別具一格,后來王應山纂《閩大記》《閩都記》,何喬遠纂《閩書》,也都襲用此法……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,有的且是未見于其他志乘的,體例也比較齊整,為我省編纂各級地方志之所本”。同樣,在明代《閩大記》和《閩書》等方志中均沒有金鯉登第的記載。
再次,從古籍文獻記載看,唐武德四年(621)發布開科舉士的敕令后,至武德五年(622)十月,諸州經過考試貢明經143人、秀才6人、俊士39人、進士30人。十一月引見,敕付尚書省考試;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主持考試,取中秀才1人、進士4人。該科進士頭名為孫伏伽,這是中國科舉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狀元,與孫伏伽同進士的還有李義琛、李義琰、李上德等3人(參見《唐摭言》卷十五)。因唐代科舉始于武德五年,所以,金鯉根本不可能登武德二年庚辰進士第。
顯然,金鯉是莆田進士第一人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,正確的說法是莆田歷史上的第一位進士為“九牧林家”林披之子林藻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