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劉愛紅
【生平介紹】 黃仲昭(1435—1508),原名潛,字仲昭,以字通稱,號未軒,又號退巖居士。興化府莆田縣東里巷(今城內(nèi)英龍街)人。明憲宗成化二年(1466)進(jìn)士,歷官翰林編修、南京大理寺評事、江西提學(xué)僉事等職。有京都“翰林三君子”“翰林四諫”之號,以忠烈士節(jié)與史學(xué)著作揚(yáng)名于世。其傳世作品有《八閩通志》《延平府志》《邵武府志》《南平縣志》《興化府志》《未軒文集》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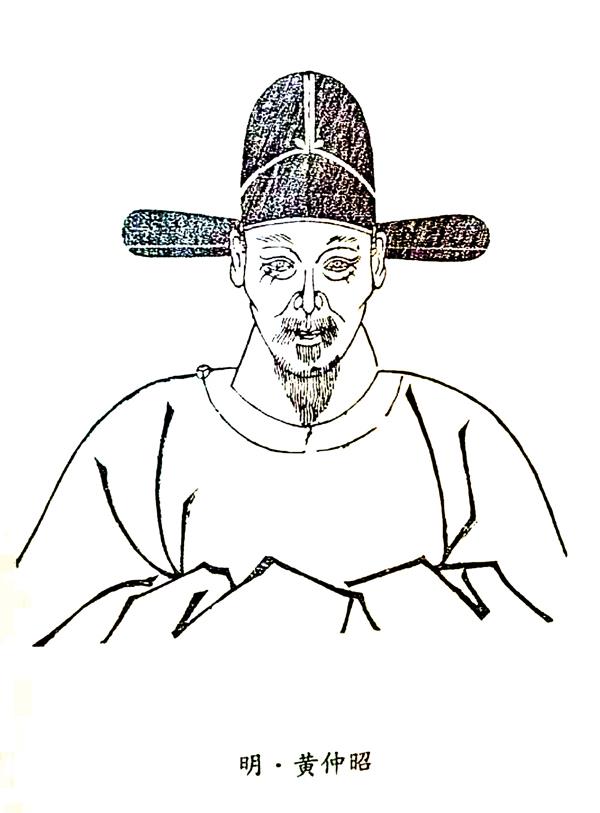
【人物亮點(diǎn)】 在擔(dān)任翰林編修時(shí),與翰苑同官章懋、莊旭聯(lián)名上疏進(jìn)諫,請求禁元宵張燈,將銀兩省下用于災(zāi)民或賞軍士。在擔(dān)任南京大理寺評事時(shí),清正廉潔,嚴(yán)于自守,不領(lǐng)虛報(bào)空額的俸祿;復(fù)核案件,堅(jiān)持法紀(jì),公正無私,不徇私情,對不符法紀(jì)案件反復(fù)論駁,務(wù)盡實(shí)情,給予平反。在任江西提學(xué)僉事時(shí),考選生員職事,嚴(yán)格考試,公正取舍,以品行第一,文章第二,品文校行毫發(fā)不爽,對宦家子弟無所寬容。完成考選生員職事后,上疏乞請放遣致仕獲準(zhǔn),郡邑師生贈禮為其餞行,他一無所受。他一生仕途雖不得志,仍自強(qiáng)不息,潛心著述,在史學(xué)領(lǐng)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【金句摘錄】 初登進(jìn)士第,抒發(fā)獻(xiàn)身報(bào)國的丹心,詠詩:“平生一片丹心在,擬獻(xiàn)君王贊廟謨(朝廷的國計(jì)方略)。”“小臣未效涓埃報(bào),但誦用詩答至仁。”
任翰林編修時(shí),憂國憂民,與章懋、莊旭聯(lián)名上疏請罷元宵煙火,寫道,“若今煙火之舉,恐非‘堯舜之道’;煙火之詩,恐非‘仁義之言’。”“省此冗費(fèi),以活流離困苦之民,賞征戍勞役之士,則干戈可息,災(zāi)旱可消,百姓可以富庶,四夷可以賓服,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。”
任南京大理寺評事時(shí),清正廉潔,不領(lǐng)虛報(bào)空額的工錢,說道,“今不署名,異日得之,亦不敢受也。”;復(fù)核案件,堅(jiān)持法紀(jì),不徇私情,說道,“落罪下官,以奉迎大吏,吾不為也!”
任江西提學(xué)僉事時(shí),盡心效職,為國選才,說道:“用人莫要于提學(xué)得人,則能培養(yǎng)天下之才,為國家用。”
為興化府學(xué)鄉(xiāng)貢、進(jìn)士題名作記,論宋代莆陽進(jìn)士的成就,指出:“……臨大節(jié),則蹈鼎鑊而不顧;決大議,則觸權(quán)奸而不恤……”勉勵題名者,當(dāng)為莆田自重:“其立朝也,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;其治民也,必求諸古之所謂循吏。世道隆平,則崇禮讓、勵廉恥,表然立天下之軌范;萬一不幸,則抗節(jié)義、殉忠孝、毅然樹國家之楨干(骨干)。”
黃仲昭修史具有鮮明的史鑒功效。在《八閩通志序》中自認(rèn)“是書之作,其文則志,其義則資治之史也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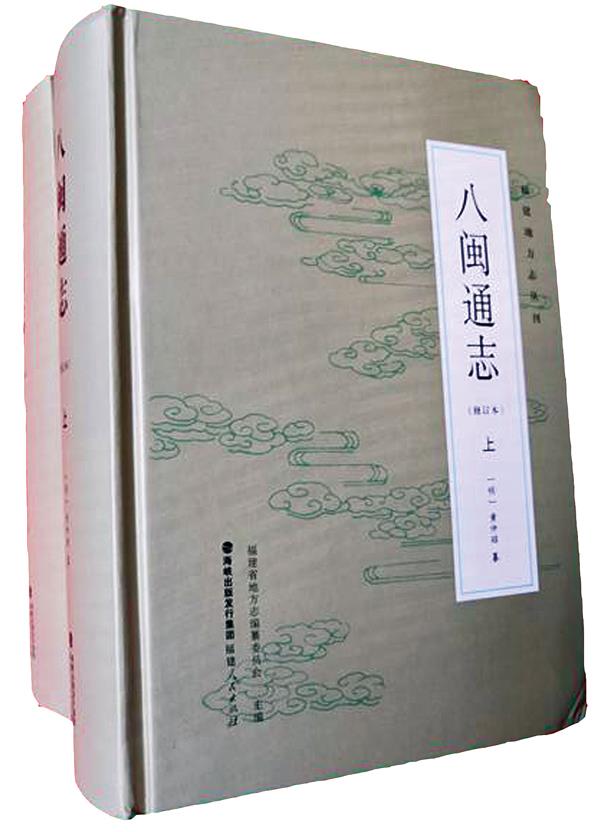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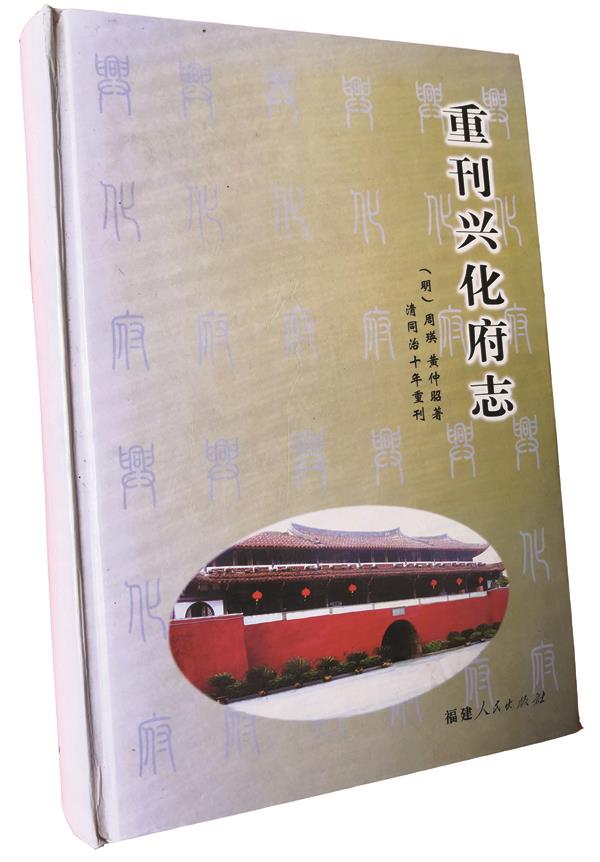
【主要事跡】
“翰林三君子”
東里黃氏是莆陽望族,黃仲昭是“東里黃”唐五代時(shí)期名臣黃滔第十八世孫,祖父黃壽生,翰林檢討,有學(xué)問和操行。父親黃子嘉,束鹿(今屬河北)知縣,因政令妥善而聞名。東里黃氏家學(xué)淵源深厚,家族清風(fēng)世代相承,名臣輩出,均為官廉潔生活簡約,為人則謹(jǐn)慎謙遜,學(xué)問文章為世人欽羨。
黃仲昭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,品性端莊謹(jǐn)慎,年紀(jì)十五六歲就有志于儒學(xué)。明憲宗成化二年(1466)他考中進(jìn)士,被選為翰林庶吉士(明朝廷選取擅長文學(xué)和書法的新進(jìn)士充任)。與同榜的羅倫、章懋、莊昶等,以名節(jié)相激勵,立志以丹心報(bào)國。
第二年,黃仲昭授翰林編修。這年的十二月,憲宗下詔令翰林院的官員依照舊詩格式寫元宵煙花燈詩,以備元宵節(jié)時(shí)賞玩。黃仲昭看那些舊詩的格式,都是玩好之物、鄙褻之詞,并非那些“養(yǎng)圣心、崇圣德”之作。而國家當(dāng)時(shí)正處于內(nèi)外交困之際,江西、湖廣,一旱數(shù)千里,民不聊生,生靈嗷嗷,張口待哺。黃仲昭憂國憂民,與同道中人翰林院同官章懋(翰林編修)、莊旭(翰林檢討)聯(lián)名上疏諫止。指出,國家正處于內(nèi)外交困的非常時(shí)期,雖然政府對旱民有優(yōu)詔賑恤,然而公私銀兩都告匱乏,正無法可想。這時(shí)候正是陛下日夜焦慮操勞,無暇顧及自身飲食的時(shí)候,同理,也是兩宮母后同憂天下的日子,決不是花費(fèi)諸多銀兩鬧元宵以燈火為樂的時(shí)候。
諫疏以相當(dāng)?shù)钠撌龊擦止賳T論思獻(xiàn)納之職責(zé)所在及其公直的舉動。指出,翰林之官,以論思代言為職責(zé)。雖稱“供奉文字”,然而不宜作粗俗淺陋經(jīng)不起推敲的煙火詩之類進(jìn)獻(xiàn)于皇上。
三人上疏中指出,他們曾伏案拜讀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院的箴言,有“啟沃之言,惟義與仁;堯舜之道,鄒孟以陳”。今日要行元宵張燈之舉,恐怕不是堯舜之道吧?讓翰林院擬作煙火之詩,恐怕不是仁義之言吧?若他們明知不可為而順著圣意去做了,那是不忠;知道不可為,而不據(jù)實(shí)上奏,那是不直。不忠不直,那罪可就大了。他們希望陛下刀下留情,寬恕他們,采納他們無知淺陋的諫議,禁止元宵張燈事宜。而省下那些冗雜的費(fèi)用,可以去養(yǎng)活那些流離困苦的人民,賞賜那些從征戍守兼在軍隊(duì)屯田勞作的戰(zhàn)士(明太祖朱元璋定下“養(yǎng)兵百萬,不費(fèi)百姓一粒米”的軍戶軍屯制),那么不但戰(zhàn)爭可以停止,災(zāi)旱可以消除,百姓可以過上富庶的生活,四方的外族也能來歸順。那樣就能安享億千萬年的太平,保持永無休止的美善啊!這也正是所謂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啊!
一封奏疏,盡現(xiàn)他們誠守職責(zé)、忠君體國、憂民濟(jì)世之心!
明憲宗見到奏疏則大怒,說元宵張燈是祖宗慣例,他不過是循慣例而已。他怒氣沖沖地斥責(zé)三人,罰以廷杖(皇帝在朝廷或殿堂上對大臣實(shí)施的杖責(zé)),貶仲昭為湘潭(今屬湖南)知縣,章懋、莊昶也獲罪被貶,一時(shí)名重京師,有“翰林三君子”之號。翰林修撰羅倫也因?yàn)橹毖哉撌拢痔査娜藶椤昂擦炙闹G”。
說到廷杖,通俗地說就是用大板子打大臣的臀部。在明代,相當(dāng)程度上是皇帝維護(hù)自己權(quán)威甚至發(fā)泄怒氣和怨氣的工具。而廷杖受刑的主要原因就是諫言。黃仲昭、章懋等之所以激昂奮發(fā),不顧自己犯言直諫,除了感恩圖報(bào)國恩,更因?yàn)槌鲇趹n國憂民之心才奮不顧身。犯言直諫是他們忠節(jié)思想的體現(xiàn),廷杖、貶官讓士林同情、贊譽(yù)。邑人周瑛贈詩為黃仲昭送行,歌頌他直諫而被謫的豪氣勁節(jié)。邑人翰林學(xué)士柯潛,連夜草疏,乞請予以寬免,為被貶黜的三臣論救,又贈詩贊揚(yáng)黃仲昭,撫慰勉勵他堅(jiān)志守節(jié)。《宋史》贊揚(yáng)黃仲昭諸人,以文學(xué)侍從為本職,并無言官的職責(zé),大可以作些應(yīng)景奉酬的詩文,安心待在翰林院,卻“激于名義,侃侃廷諍,抵罪謫而不悔”的“皎然志節(jié)”。給事中毛弘上疏抗言論諫說:“三位大臣出身草野,剛剛在翰林院任職,能奮不顧身,敢言直諫,這當(dāng)真乃盛世才會出的事兒。乞請恢復(fù)三位大臣原官職。”憲宗采用毛弘諫言,改命黃仲昭、章懋為南京大理寺(主管刑獄之政)評事。當(dāng)時(shí)黃仲昭正赴任湘潭知縣途中,于是返回就任新職。
廉潔自守 執(zhí)法公正
大理寺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(jī)構(gòu),主要是復(fù)核會審大要案。評事為七品司法官。黃仲昭氣岸屹立,風(fēng)骨錚錚,恰適合評事職位。
任上,黃仲昭清正廉潔,嚴(yán)于自守。當(dāng)時(shí)北京、南京各官署把隸卒大都放回去,而照舊領(lǐng)取他們每月的工錢成為常例,南京大理寺本有值堂守門隸卒的名額,寺官多虛報(bào)空額,分享工錢,上下相安,習(xí)以為常。黃仲昭認(rèn)為不合道義,竟不領(lǐng)取。評事官員納薪者例有二人,同官援引北京大理寺之例,欲聯(lián)名上請?jiān)黾右蝗恕V僬选⒄马詣偒@罪被貶謫正要反省過錯(cuò)為由不予署名,而且說:“今日不署名,異日得之,也不敢接受。”
黃仲昭復(fù)核案件,堅(jiān)持法紀(jì),公正無私。有個(gè)御史官放縱子侄晚輩犯法,辦案者曲意包庇他們。黃仲昭堅(jiān)持執(zhí)法,不許法外開恩。有富家兄弟互相訴訟,黃仲昭查清他們家器物多是違法所得,應(yīng)當(dāng)沒收入官。該富民廣加交游,得到庇護(hù),又暗地通過黃仲昭的私交,請求從寬處理,仲昭亦不許。戶部有一個(gè)下屬官吏,被監(jiān)倉的上官誣陷。黃仲昭說:“落罪下官,以奉迎大吏,吾不為也!”也不允許。又有數(shù)人為盜,入室未得財(cái)物,就將那家的主婦綁去,共同奸污后又將她販賣。辦案人只將首犯處以死罪,其余則以他們未得財(cái)物而從輕發(fā)落。黃仲昭復(fù)核時(shí)認(rèn)為,害人之罪,重于得財(cái)。罪犯不但把那家婦人綁走,還污辱并把她販賣了,而稱未得財(cái)物給以從輕處罰,這可以嗎?也絕不允許。黃仲昭執(zhí)法,對不合法的堅(jiān)決不許放過,都是反復(fù)論駁,務(wù)盡實(shí)情,所、司亦多贊同所斷,終歸于公正。因此受到平反者的稱許,而嫉恨者亦為數(shù)不少。
明憲宗成化九年(1473),黃仲昭三載任期屆滿,升大理寺左寺副(從六品)。申請回莆省親。居家半載返朝。成化十一年(1475),相繼丁父母憂(古代,父母死后,子女按禮須持喪三年,其間不得行婚嫁之事,不預(yù)吉慶之典,任官者并須離職,稱“丁憂”),守制前后四年,至成化十四年(1478)二月守喪期滿除服。其間因患傷寒轉(zhuǎn)成勞疾,延醫(yī)調(diào)治,至成化十五年十一月痊愈,隨即起復(fù),于成化十六年三月到吏部。
黃仲昭此行,并非待命任官,而是決意請歸養(yǎng)病。有人勸他留任,仲昭堅(jiān)守清節(jié),厭惡阿意為官,以養(yǎng)病為由堅(jiān)請歸田。致仕(交還官職,即退休)歸莆后,黃仲昭買田筑屋于城南下皋山中,為耕讀之所。閑時(shí)則與田夫野老談笑共酌,既忘官身之貴,又忘生計(jì)之貧。鄉(xiāng)里嘗有人請其為私利疏通關(guān)節(jié),仲昭甚力拒之,鄉(xiāng)人由此知其為人,后來就不再求他說情了。
仲昭作《下皋雜詠》二十四首,記述深居山林的田園情趣。詩中不乏對仕途的厭倦追悔情懷,然憂世憂民之心依然故我。
黃仲昭居山十年,自求其樂,勤于讀書著述。明成化二十年(1484),主編《八閩通志》,歷經(jīng)六年始成書。
考錄人才 品行優(yōu)先
明孝宗弘治元年(1488),吏部尚書王恕奉詔起用黃仲昭。黃仲昭在完成編纂《八閩通志》后,于三年(1490)起程到京。參拜吏部時(shí),尚書王恕親自到門口迎接,拱手恭讓進(jìn)入廳堂,二人相向再拜,禮遇甚優(yōu)。因當(dāng)權(quán)者皆是仲昭在翰林院時(shí)的同僚,對仲昭心懷宿怨,加以阻撓,故未能大用,而出任江西提學(xué)僉事(即以按察司僉事充任提督學(xué)官)。仲昭雖感不遂人意,仍盡心效職。曾說:“用人莫要于提學(xué)得人,則能培養(yǎng)天下之才,為國家用。”
任上,黃仲昭用正統(tǒng)的儒學(xué)教誨士子。他考錄人才標(biāo)準(zhǔn),都是以品行第一,文章寫作技藝倒在其次。
為便于士子們學(xué)習(xí),黃仲昭選定善本,翻印、新刊。又制定冠(成年)、婚、喪三大祭祀的儀式,刊印發(fā)布,為后學(xué)示范。同時(shí),嚴(yán)格考試,公正取舍,品文校行毫發(fā)不爽,對宦家子弟無所寬容,以至有人感到不便。
黃仲昭任職兩年時(shí),嘗賦詩感懷,生當(dāng)年彷徨心態(tài),重萌歸意。鄭岳《莆陽文獻(xiàn)》名臣傳稱:“仲昭升江西提學(xué)僉事,拳拳教人以行實(shí)為先。值額例行,簡汰太嚴(yán),物論嘩然。仲昭亦自以與時(shí)不合,再疏乞致仕。”可見,黃仲昭在江西提學(xué)任上以拳拳之心為國家培養(yǎng)人才,強(qiáng)調(diào)做人首要是行為樸厚。他自身堅(jiān)持原則,務(wù)實(shí)清廉,將不必要的額例盡行精簡,但是觸動了大多數(shù)人的利益,引來眾人議論,大表驚訝和不滿,也導(dǎo)致不合時(shí)宜,孤立于政治圈外。
明孝宗弘治八年(1495),黃仲昭在完成考選生員職事后,上疏乞請放遣致仕。他在這個(gè)職位上操勞了四年多時(shí)間,二疏獲準(zhǔn),喜形于色。郡邑師生贈禮為其餞行,仲昭一無所受。
致力修史 嘔心瀝血
黃仲昭回莆后,仍居住下皋山莊。時(shí)隔十載,原有的俱樂亭一片荒蕪景象。黃仲昭呼童仆除草剪竹,修整一番,登俱樂亭觀景,感慨萬千,詩興大作。“要放南山翠色來”,為解脫官場羈絆,回歸自我天性感到快慰。
仲昭居家,仍以讀書著述為樂事。“讀罷殘書無一事,閑調(diào)綠綺和樵歌。”(《下皋俱樂亭匾》之六)。
黃仲昭晚年,雖體弱常病,依然努力,以余生精力,致力修史。明孝宗弘治十年(1497)春,應(yīng)延平知府孫衍之請,赴南平主纂《延平府志》,歷七十日而脫稿。弘治十四年(1501),應(yīng)興化知府陳效之請,與周瑛共修《興化府志》,周瑛纂總志,仲昭領(lǐng)人物志,十六年(1503)書成。弘治十八年(1505)三月,邵武知府夏英懇請黃仲昭赴邵,主纂《邵武府志》,歷時(shí)十個(gè)月書成。又纂修《南平縣志》。為福建的方志事業(yè),嘔心瀝血,鞠躬盡瘁。
明武宗宣德三年(1508)十一月,黃仲昭積勞成疾,病卒于家,終年七十四歲。家人將其遺體安葬于華亭云峰。此墓至今保護(hù)完好,可見興化人民對他的敬仰。
【啟示】
按現(xiàn)代語言解讀,黃仲昭是個(gè)不會為官、不合時(shí)宜的人物。他居官端正,走的是正直之道,嚴(yán)于法守,憂國憂時(shí),而為當(dāng)時(shí)人所忌諱。不論在翰林院、在法司、在提學(xué),始終憂國憂民,堅(jiān)持原則,風(fēng)骨錚錚,雖屢受遭折,仍不改素志。
當(dāng)年一同在翰林院任職后為吏部尚書的林瀚,稱道他壯年時(shí)英邁之氣,忠烈可嘉。
翰林院上疏諫止罷燈火時(shí),他又何嘗不知道后果。但是,一旦他認(rèn)為上言諫止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,則振策長驅(qū),一往無前,毫不顧忌。初入官場,他明知應(yīng)明哲保身,寫些應(yīng)景文字了事,但為國計(jì)為民計(jì),他勇觸逆鱗,觸怒皇帝,即使墜入深淵也不后悔。
任南京大理寺評事時(shí),他清正廉潔,不領(lǐng)虛報(bào)空額的例錢、工錢,說今日不署名,異日得之,亦不敢接受。說到明朝的薪酬制度,草根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一反唐宋優(yōu)待士大夫的數(shù)百年慣例,開了帝國朝廷對公務(wù)員實(shí)行底薪制的先河。按照吳思先生的計(jì)算,明帝國的縣官月薪不過1130元,以至于奉公守法成了大問題,縣官海瑞為了慶祝母親生日,買了兩斤肉,竟然驚動了總督胡宗憲。京官要靠地方官進(jìn)獻(xiàn),地方官收取賦稅過程中通過收取火耗、折子銀中飽私囊成了公開的秘密。黃仲昭除了薪酬之外,一無所取,成了官員圈子里的另類,你不人從眾,必然招忌。加上復(fù)核案件,堅(jiān)持法紀(jì),不徇私情,就更招人嫌了。他辦事公正無私,不許包庇,不許違法,不許講私情寬處,不許自己落罪下官去奉迎大吏,不許不公審判。更不怕得罪人,風(fēng)骨錚錚,磊落分明,平反者稱快,嫉恨者積怨。
提學(xué)僉事職權(quán)在明朝時(shí)相當(dāng)于分管教育的御史,兩京,北京南京以御史擔(dān)任,十三省以按察司僉事充任提督學(xué)官,對選拔人才上至關(guān)重要。黃仲昭懷拳拳之心為國選才,講原則,講人品,再講學(xué)問,即使是宦家子弟亦不徇私情,這在官員圈子里必然招忌招嫌招恨,利益使然。他為學(xué)子們刊印善本、定禮儀,莫不是為了學(xué)子著想。
黃仲昭當(dāng)官期間,想為國家,為百姓做貢獻(xiàn),而身不由己,又不愿與腐敗的當(dāng)權(quán)者同流合污。退休后,就“日事著述”,“以畢其初志”。他“旁搜博考”,接觸人民,考察歷史遺跡,廣泛搜集史料,寫下煌煌史冊,為福建和興化人民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(chǎn)。他修史具有鮮明的史鑒功效,是為了實(shí)現(xiàn)其早年痛感士習(xí)民風(fēng)不古,欲以先哲典范事跡風(fēng)勵后學(xué),以補(bǔ)世道風(fēng)俗的宿愿,修《八閩通志》自認(rèn),“是書之作,其文則志,其義則資治之史也。”
黃仲昭還是明代文壇一位重要的詩人。在為官期間及游歷考察期間,廣泛地接觸了社會實(shí)際,對民生的苦難、吏治的腐敗,體會頗深。這些在他的詩文中都有反映,表達(dá)了作者對百姓疾苦的同情和關(guān)心。一代名臣,視宦海沉浮淡然處之,終身矢志于修志、經(jīng)學(xué)與文學(xué)。
縱觀黃仲昭一生,他忠誠篤實(shí)踐行古代士族精英“修身、正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政治理想與人生軌跡,且身體力行,進(jìn)不求祿、退不避事,淡泊名利,堅(jiān)持氣節(jié)、坦然進(jìn)退。這給當(dāng)今的我們頗多啟示。
講家風(fēng),他一家從遠(yuǎn)祖至祖父至孫輩,簪纓連綿,名臣輩出,為莆田望族之冠,可見家族清風(fēng)世代相承的重要性。
講為官之道,為人風(fēng)范,他是當(dāng)今人們學(xué)習(xí)的典范。古語講,“政聲人去后,民意閑談中。”從古至今,為官者的價(jià)值都承載于奉公為民上,體現(xiàn)在民意口碑中。黃仲昭懷抱范仲淹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胸襟,一心為國為民。一生理想追求堅(jiān)定,甘于奉獻(xiàn)、甘于平淡,不追名逐利。用現(xiàn)代的說法,他是一名優(yōu)秀的人民公仆。
不同的歷史時(shí)期,面對不同的時(shí)代任務(wù),無數(shù)人民公仆應(yīng)踏著歷史前進(jìn)的節(jié)拍,堅(jiān)定信念、勤政務(wù)實(shí),奉公為民,清廉自守,涵養(yǎng)公心,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(yán)私德,淡泊名利,勤勉奉獻(xiàn)。“一切為民者,則民向往之。”在奉公為民的價(jià)值坐標(biāo)上,開拓更為豐盈的人生空間,成就造福一方的偉業(yè)。

